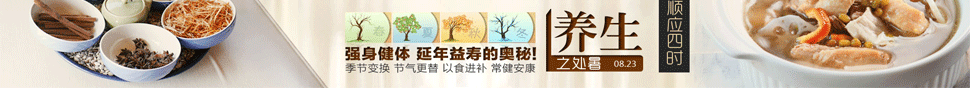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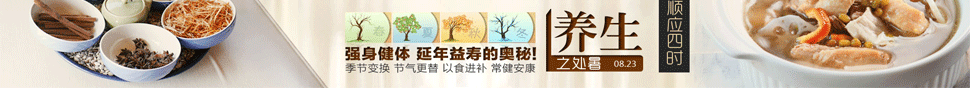
中小企业(ID:sinosme)联合红楼梦文化经济研究会开辟“红楼经济说”专栏,依据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真金白银说红楼》、海天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经济学》以及作者在《深圳特区报》“理论周刋"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分为各自独立主题以连载的形式奉献给大家。
假如《红楼梦》中人去摆地摊,谁是王者?谁会倒闭?
现在讲“地摊经济”,这是符合“生活经济”法则的。生活即经济,没有超越于生活之外的经济。可惜现在的经济发展脱离了生活的层面,搞了过多的脱离生活本身的东西,实践证明那是行不通的。
这使我想起了《红楼梦》,想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状态下贾府的“府邸经济”。那个时候,贾府还不至于摆地摊,但贾府有一帮负责府里膳食的家佣见过地摊,买过地摊,地摊在京城是随处可见的。北京作为全国最大的消费性城市,这里不仅有全国最大的商业市场,而且聚集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向被称作“商贾辐辏之区”。而京城消费型城市的特点,也使它形成了商业比手工业发展,官商优于私商等特点。而在众多的商人中,他们通常都以“铺户”作为个体从事商业活动的。所谓“铺户”,是指开店铺的人户而言,是当为封建政府从户籍管理的角度对商人的称呼。由于店铺是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铺户的称谓也应当在封建社会后期才出现,清代官方文献《清实录》中就有“铺户”的记载。近日读周果先生的《当代北京广告史话》方知北京有很多街道和胡同都是早先的农贸集市,如鲜鱼口、骡马市、果子巷、菜市口、花市、灯市口、米市大街、东江米巷(现东交民巷)、西江米巷(现西交民巷)。这些集市都是自发的,没有人管理,先是几个人摆摊卖货,后来摆摊的越来越多,就形成了集市。这些自发的集市跟客流稳定的店铺和走街串巷的游商不一样,他们用不着字号招牌,用不着幌子,也不用费力费神的吆喝,只要把出售的货物在集市上一摆,顾客就上来问价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买卖双方就可以成交。这就是地摊经济的威力。
明末清初,花市大街住着很多以做纸花、绢花为生的家庭工业者。他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简单分工,妻子或母亲裁剪纸张,丈夫或父亲扎花束花,加工出来的假花多是供给宫里或商铺,这些家庭手工业者赚点辛苦钱。由于挣得很少,加上做好的假花经常被采购者以各种理由退回来,这些手工业者便把自己积压的假花拿到街上出售。路过的市民发现这些假花很漂亮,可以永久摆放,价格又实惠,真花贵不说摆放几天就死掉了,于是就开始购买假花。一来二去,街头上买花卖花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花市的名字就叫开了。《燕京岁时记》对花市有这样的记载:“所谓花市者,乃妇女插戴之纸花,非时花也。花有通草、绫绢、绰枝、摔头之类,颇能混真。”
贾府后来因罪被抄家,一府经济然轰然倒塌,一贫如洗,贾府的人们死的死,散的散,落得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这时候,叫府里剩下的人去摆地摊其实并不为过。许多“红楼梦续书”中都有这样的情节。
那么,贾府里的哪些人适宜摆地摊,在地摊经济中过活、成长呢?依我看,首推的就是贾宝玉。首先,他有贫民意识,有贫民视野,而且体验过地摊,至少对地摊不陌生。你瞧,第二十七回里记载,妹妹贾探春想买“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东西,贾宝玉随口就答“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五百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一车来”。可见他对京城地摊状况了如指掌,细说端详。他的那些“斗方”墨宝和贾府过去由鸳鸯保管着的铜锡家伙和大小器物都是抢手货,不愁卖。加上宝玉熟人多,人缘好,他要是摆开地摊,那一定是京城一道靓丽的风景。这里多说几句,贾宝玉怕是先天与地摊有缘,他去和茗烟去北静王爱妃的坟头祭拜,没有香了,就嘱咐茗烟到四周转转看,有没有卖的;他在秦可卿出殡的铁槛寺周边的农庄里,他是访贫问苦,对农人极尽关怀,对纺则之事亲自体验。书中写道:“凤姐进入茅屋,先命宝玉等出去玩玩。宝玉会意,因同秦钟带了小厮们各处游玩。凡庄家动用之物,俱不曾见过的,宝玉见了,都以为奇,不知何名何用。小厮中有知道的,一一告诉了名色并其用处。宝玉听了,因点头道:‘怪道古人诗上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正为此也。’一面说,一面又到一间房内。见炕上有个纺车儿,越发以为稀奇。小厮们又说:‘是纺线织布的。’宝玉便上炕摇转。只见一个村妆丫头,约有十七八岁,走来说道:‘别弄坏了!’众小厮忙上来吆喝。宝玉也住了手,说道:‘我因没有见过,所以试一试玩儿。’那丫头道:‘你不会转,等我转给你瞧。’”。这一切,都是他热心于做小本深意的“心灵土壤”。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如贾政、贾赦这些人,叫他们摆地摊只能饿死。
贾府的其他人,如贾琏、贾芸、贾蔷等等,都是沉不下心的人,贾琏只是个主子气十足的人,颐指气使,对下人发号施令,还要讲享受,捞好处,容不得半点儿不同意见,即使是到王熙凤那儿,也是使爷儿气,耍派头;贾母那儿,也极尽敷衍,糊弄讨好,不讲真话,不干正事。他是十足的爷们,没有摆地摊的心态。贾芸、贾蔷那几个,凡事挑肥检瘦,油锅里捞三捞,专打别人的坏主意,他们是极端利己主义者,而且还讲究“面子”,坑蒙拐骗可以,指望他们公平交易,赚辛苦钱,门儿都没有。
当然,贾府摆地摊,贾探春是最合适的一个。她坚守“物用价值”经济观,开源节流、精打细算的作风,推行大观园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做派,都是她“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民生物用思想的自然流露和具体体现。书中第二十七回记载:探春想要些女孩子家喜欢的小玩意,还要自己攒钱,请宝玉帮忙买回来。宝玉听后却笑说都是不值钱的东西,让小厮来买可以拉一车来。而探春是怎么说的呢?“小厮们知道什么?你拣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这些东西,你多多的替我带了来.我还象上回的鞋作一双你穿,比那一双还加工夫,如何呢?”从这些细小的情节里,我们可以看出她有做好“地摊经济”的朴实感情,也具备干好这一行的能力和耐心。只是未等到贾府落败,她却远嫁异国他乡了,不好比拟。
《红楼梦》中还有一位皇商,就是薛蟠,后来贾府落败,薛家也敗了。薛蟠是沾祖上的光,挥霍无度,滥交朋友,野性十足,尤其是喜欢亲近女孩子,花天酒地,打打杀杀,要是把地摊给他,不出一天保准地摊儿不见了,还不知要惹出多少是非来。在第四十八回里,写他和自家当铺的“总管”张德辉出远门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带多少本钱?找哪些故旧?想必精明的薛姨妈和思虑过人的薛宝钗是做出了详尽的安排的。可好几个月他俩回来,就一无所获,只给同辈的妹妹们带点小玩意礼品。
薛蟠出远门去做生意,家里的老伙计张德辉告诉他:“今年纸扎、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贵的……顺路贩些纸扎、香扇来卖。”纸扎,也是丧事上用的。这一行业,应该是薛家的主营。想必,秦可卿的葬礼,薛家也赚了不少银子。第三,香料。正如张德辉所言,香料也要沿途贩些来,证明薛家应该还有一家专门卖香料的铺子。只不过,不知道这家铺子的规模如何。想必,要比贾芸的舅舅卜世仁的香料铺,大的多了。第四,药材。第七十七回,当王夫人要替王熙凤配调经养荣丸的时候,需要上等人参二两,王夫人四处找寻不到,正要让周瑞家的去买,薛宝钗道:“姨娘且住……我们铺子里的人,常和参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妈说了,叫哥哥去托了伙计过去,和参行里商议说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参兑二两来……”薛家常和参行交易,肯定不可能仅仅是为了自己家里吃,更多的情况下,是因为店铺的需要。所以,薛家应该还是有一家药材铺的。守着这么多行业的生意,若是薛蟠是个精明能干的,薛家何至于一步步走向衰落?要是他去做地摊生意,一定是个最大的输家。
《红楼梦》中贾母擅长于边际决策贾母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边际决策”,即特别长于通过比较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来做决策。
《红楼梦》中的贾府是个大家庭,人口逾千,大事小事不断,迎来送往,涉朝廷也关乡野。贾府类似于现如今的一个集团公司,其总经理是王熙凤,她是十足的经理人,是管理事务的能手,尤其在理财方面堪为高人。但就管理思想、经济思维方面来说,还是“董事长”贾母技高一筹。
贾母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边际决策”,即特别长于通过比较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来做决策。虽然她所处的时代在清早期,还没有接触到当代经济学大家曼昆的理论,但却以自己独到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为曼昆的经济理论提供了注脚。
贾母的饮食是讲究的,她老人家吃天上飞的、地里跑的,都十分刁钻和讲究,按现在通常的解释,是她“考究”,是她改不了“精细雅致”的生活习性。即使按中国传统文化去给她安个头衔,那也至多是“居宜气,养宜体”等一些儒家的学说,一点也沾不上人的经济层面,而“人”在社会上首先是“经济人”,是很物质和平实的个体。那贾母的个人生活为什么要那么奢华和讲究呢?曼昆的解释是:“当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时,你面临的决策不是在完全不吃和大吃一顿之间的选择,更可能的是你将问自己‘是否再多吃一勺土豆泥’”。曼昆是说“多吃”,而贾母是“少吃”,吃得精细些、珍贵些,道理都是一样的。那么。多吃或少吃是为了什么呢?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和盘算?那当然有许多“边际”的考量,牵涉到“边际决策”问题。曼昆先生还有一段很有名的话:“这里有个经典问题:为什么水这么便宜,而钻石如此昂贵?人需要水来维持生存,而钻石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但由于某种原因,人们愿意为钻石支付的钱要远远高于水。原因是一个人对任何一种物品的支付意愿都基于其增加一单位该物品所获得的边际收益。”
那贾母在府上经济遇到困难时,为什么又停下了自己一贯享用的“玉田胭脂米”和各房送过来的“捧盒”(装的是膳食)呢?这也有个边际效应的问题。是继续吃它还是蠲之不用,都有经济考量,都有边际的取舍。
贾府还是囤积洋货的“大仓库”,而这方面贾母又是集大成者。她老人家自己享用玻璃炕屏这些洋巴巴的玩意不说,还鼓励和推动自己府上消费。孙儿宝玉穿的用的,王熙凤贮存的、享有的,丫鬟仆佣们痴迷的、追捧的无不是洋货。那时清朝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不参与世界流通,自己土地上生产的东西不值钱,而国外由于先进的技术和制造工艺,生产出的东西十分抢手,贾府属于大清的上流社会,自然成了洋货物品的追捧者和享有者。这不需要用现行的那种“盘剥、压榨、奢靡”等符号来解释,用曼昆的“钻石和水”的理论来解释和疏通就容易得多。贾府为购买这些洋货是要花去很多钱,甚至有人说“需要支付贾府一半以上的积蓄”。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贾府是位列公侯的王公贵族,那他拿什么去区别于一般人家,区别于其他豪门大户?使用洋货,使用这些见都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才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此其一;其二,就是这些东西和庄头乌进孝他们送来的东西相比,具有精细、美感和经久耐用性,是新潮的物品、持久的物品、充满艺术美感的物品。
曼昆先生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举了一个打折坐飞机的例子。假如一架有个座位横越美国飞行的飞机,航空公司的总成本是10万美元,平均每位机票是美元。那美元一张的机票能不能卖?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假设机票有剩余,卖出的机票亏空的钱,那只是“这位额外的乘客消费的一包花生米和一罐软饮料的成本而已。”,即所谓“边际成本”。曼昆进一步指出:“只要等退票的乘客所支付的钱大于边际成本,卖给他机票就是有利可图的”。
《红楼梦》中的贾母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在那个时代,王侯贵族进退排列都是变动不居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如同坐飞机一样,卖打折票的、退票的,有的是。这里面“边际成本”可以不要多去考虑,只要努力去争取“机会效益”就行。书中写贾府赢得的这种“机会效益”的例子多的是,贾母是为这个五世不败,繁花似锦之家深谋远虑啊!不要总习惯从固有的阶级性,抽象的“标签”去贴贾府,也不要拿平常的眼光去看贾母,去分析《红楼梦》中那么多的事、那么多人物的行为,这样肯定会陷入感性的泥潭和沼泽,说不清道不明,甚至会前后矛盾,落入不能自圆其说的窘境。
经济的事用经济的理论去说,用经济的理论去分析和梳理、归纳,这正是“红学”研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作者:张麒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决策咨询智库研究员。二十多年来,潜心《红楼梦》及中国国学和古代商业研究,成果颇丰,著有《红楼梦经济学》《真金白银说红楼》《红楼梦菜谱》《古典的魅力》《中国古代商人的智慧》等著作。尤其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在学界颇有影响,被誉为“红楼梦经济学产业化研究第一人”。
sinosme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xiaotongcaoa.com/yfyl/7865.html


